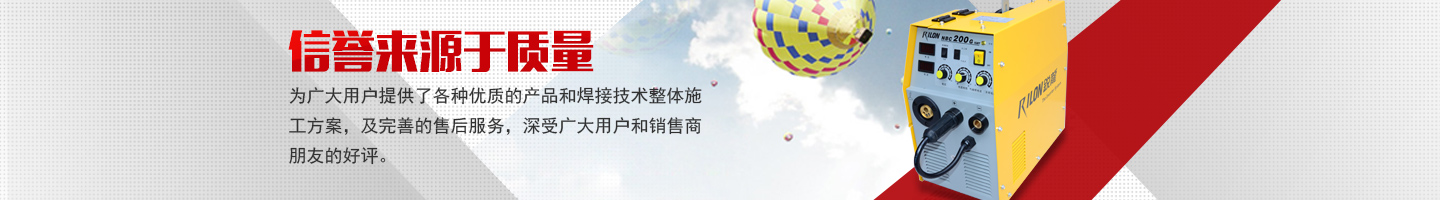
黄河是华夏母亲河,这个名字看似和蔼可亲,但现实中却并没有那么慈祥,“三年一改道”几乎成了世人皆知的自然灾害;也正因如此,数千年来由于黄河泛滥而消失的古迹举不胜举,例如商丘地下“城摞城”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,征服黄河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丰功伟绩之一,其中就包括架桥;蒲州古城的黄河边就矗立着四尊“铁牛”,历经千余年,又在黄河水中浸泡数百年,但至今仍“不肯生锈”。
黄河铁牛位于今天的山西永济市西十五公里处,大致在蒲州城黄河古道两岸;追溯历史,蒲州是历代联通秦晋的交通要道,也是历史上的“第一黄河渡口”。《春秋左传》有记载“秦公子咸奔晋,造舟于河”直白点解释,这里的“造舟”指的就是最早的蒲津浮桥;说到这或许有朋友要说了“这不古人也能在黄河上架桥嘛,至于单独把铁牛拿出来介绍吗?”这里解释一下,自古黄河多泛滥,别说架桥,就是撑船行舟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;而且蒲津古桥只能说是一座临时性的浮桥,能使用满一年就算是奇迹了。
唐时河东为京畿,蒲州成了长安与河东的重要联系枢纽,尤其到了开元六年,蒲州还被唐皇设为中都,与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齐名,由此在黄河上架桥就成了朝中大事;这还仅是一方面,除了与外界联系外,还有行军打仗和巩固政权的需要,尤其唐王朝对于河东和整个北方地区的实际控制,更需要一座联通外界的“黄河大桥”。直到唐玄宗时期,蒲津渡口终于“改木桩为铁牛,换竹索为铁链,疏其船间,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。”
展开剩余76%乍一看似乎仅是铸造了几尊铁疙瘩而已,至于说成是“大规模改建”吗?要回答这个问题,答案还得从这几尊铁牛身上找;大体来讲,每尊铁牛高约1.9米,长约3米,宽约1.3米,牛尾后有横轴,直径约0.4米,长约2.3米,分别有连珠饰、菱花、卷草、莲花等。铁牛的造形生动逼真,作前腿蹬状,后腿蹲伏状,就好似真牛在用力拉扯一样,牛体矫健强壮,尾施铁轴,以系浮桥;腹下有铁山,各重约40吨。
实事求是的说,一尊铁牛重40吨,对于一般的河流,这样的重量似乎够用了,但对黄河来说,40吨还远远不够,因此黄河铁牛也远不止几十吨重;这里解释一下,40吨仅是露出表面的重量,铁牛下面还有玄机,在每尊铁牛的底部,人们看不到的地底下还有6根,每根粗0.4米,长4米的铁柱子,其作用类似于地锚。再加上铁牛身下的铁山和铁人,其总重超过了200吨;史料记载,最初的黄河铁牛并非今天的四尊,而是八尊,这样的规模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,足称“浩大”。
简单换算一下,如果一尊铁牛重达200吨,那么八尊就是1600吨,值得强调的是,据考古推测,盛唐时期的铁年产量不过1千吨左右;试想,仅八尊铁牛的用铁就超过了唐王朝一年的产量,此外还有铸造、架桥等等后续工程,由此足证蒲津渡黄河铁索桥的恢弘规模。这里还有个问题,古代没有起重机,这八尊铁牛又是怎么运到黄河边的呢?懂行的朋友或许会说“这还不简单,现场铸造呗”,乍一看似乎很容易,专家也的确发现了遗址内有许多古代小铁炉的痕迹;但是,考古专家却说:八尊铁牛的铸造,至今仍旧是科学谜题。
熟悉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,真正意义上的铁器约出现在汉武帝时期,但是冶炼技艺相对落后,直到盛唐时期虽有发展但仍旧产量不高,其年产量千余吨就是证明;再回到蒲津渡口,如果唐代工匠在现场铸造铁牛,首先就要在现场冶炼出至少1600吨的铁水。这样的工程量可不是一两个人,甚至是一二百个工匠短时间内就能完成,之后还有浇灌成型,且要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牛、人形象;暂且不说铁牛的铸造技艺如何,整座黄河铁索桥落成完工,其耗时至少也要数十年之久,这里还有个关键因素,黄河泛滥可容不得大量工匠在现场铸铁,那么这八尊铁牛究竟是怎么铸造出来,又如何运到黄河边的呢?
史载,黄河铁牛一直是蒲津渡的重要组成部分,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均以此桥为重要交通线,直到元代因战争被毁,且黄河再次改道逐渐将其掩埋;据蒲津渡当地老人回忆,上世纪二十年代,每逢黄河枯水季,下水还能摸到铁牛的牛角,甚至多有船只被水底牛角挂住的情况发生。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,三门峡水库蓄洪,河床淤积,再加上河水西移,到了六七十年代,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下2米有余的河滩中,此时距离盛唐已过千年之久;理论上说,铁器遇水容易锈蚀,以元朝为节点,且不说之前的锈蚀程度,仅是逐渐淹没在黄河水中这数百年的时间,就足以使这八尊铁牛腐蚀殆尽。
1988年的考古专家同样抱有这样的想法,因此“打捞黄河铁牛”的争议一直很大,围绕的中心就是它的腐蚀程度,其“文物价值”是否还有必要打捞出水;1998年8月,由永济市博物馆在蒲津渡遗址发掘出四尊铁牛、四个铁人、两座铁山和一组七星铁柱,现场众人惊得哑口无言,历经千余年,且又在水中浸泡了数百年的黄河铁牛,出水后居然“不生锈”。当然,毕竟是铁制品,要说一点不生锈也不可能;令众人奇怪的是,四尊铁牛的锈蚀程度远远超出了考古专家们的预判,除了表面一层轻微水锈外,其余部分均保存完整。
说到这或许有朋友开始嘲笑了“连这都解释不了还当什么专家,黄河中富含泥沙,又是流动的,这就造成了泥沙和铁牛常年摩擦,就是有铁锈也早被泥沙冲刷干净了。”乍一看,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,但仔细想又觉得哪里不对;首先,这些铁牛矗立黄河边千余年,在还没有淹没的时候就已经常年与水汽接触,其腐蚀过程早已开始;其次,铁牛并非突然被黄河淹没的,而是一个长时间的浸泡过程,这样又是数百年与水直接接触,如果说泥沙可以冲刷掉淹没部分的铁锈,那么没有被淹没的部分,理论上也会腐蚀严重才对。
但是,这四尊铁牛经过简单处理后,呈现的仍旧是一副近乎崭新的样子,就连文物保护的措施也十分简单,每两年涂抹一次缓蚀剂;实事求是的说,缓蚀剂不过是一种日常维护的手段而已,想在水气弥漫的黄河边让铁器完全不生锈,理论上是不可能的,至于这四尊黄河铁牛为什么“不生锈”,专家至今难以解释。
发布于:天津市